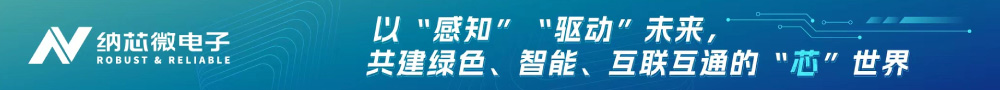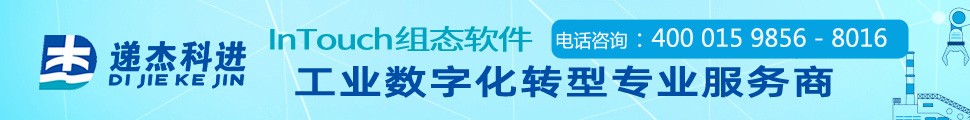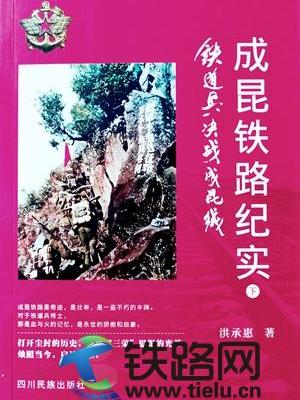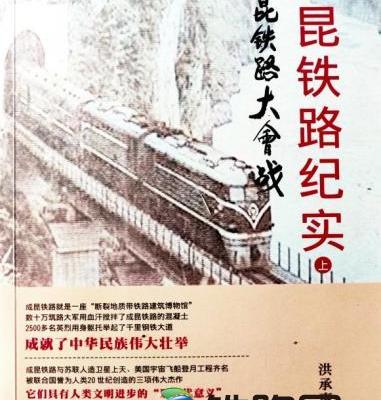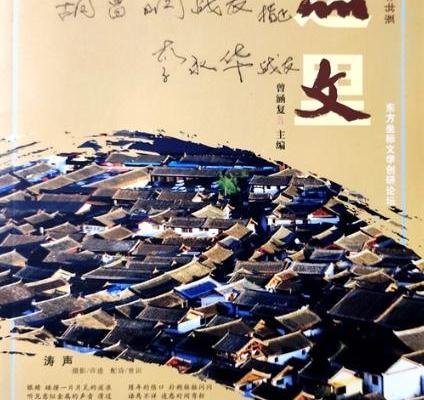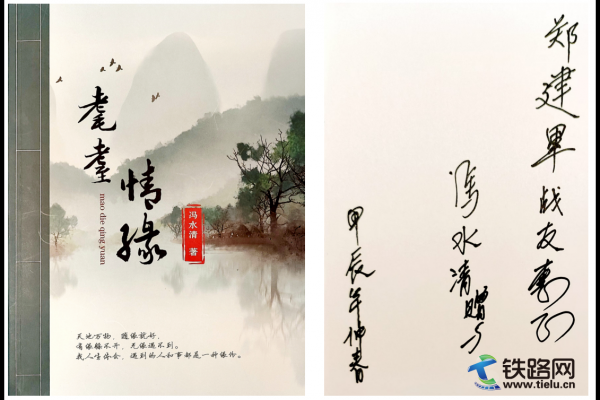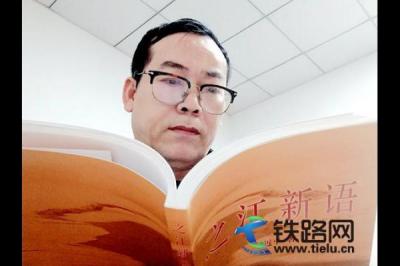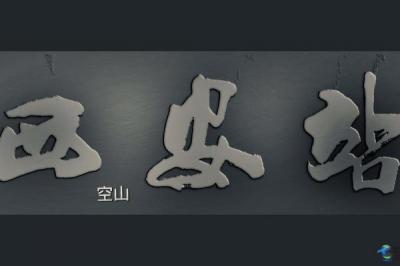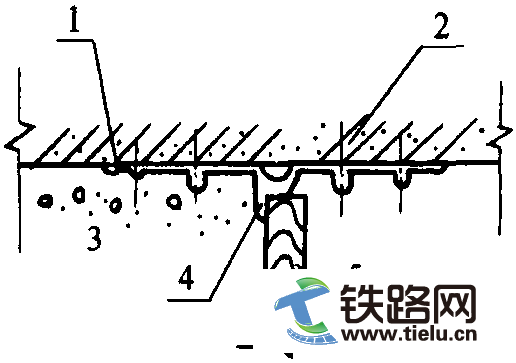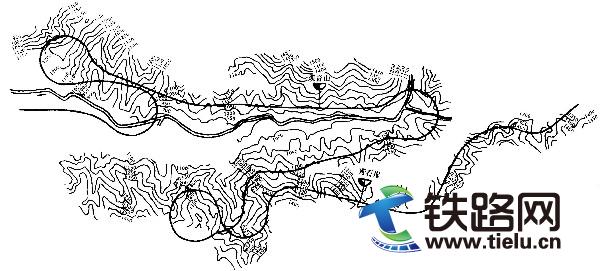1
烏蒙山區(qū)的秋晨,寒意總比陽光先一步抵達(dá)。敬穗兒工裝褲左口袋里那一小罐幾乎凝固的防銹油,在濃重的晨霧中析出了細(xì)密的冰晶,像撒了一把碎鉆。她半跪在望江2號(hào)橋冰冷的水泥基座上,額頭抵著微涼的安全帽,呵出的白氣迅速消散在風(fēng)里。扳手精準(zhǔn)地與一顆M24螺栓咬合,隨著她手臂沉穩(wěn)的發(fā)力,“咔嗒”一聲脆響,力道透過扳手傳到掌心,也驚飛了巖縫里一只羽毛蓬松的鷦鷯,撲棱棱地消失在大山深處的幽暗中。
這個(gè)檢查、緊固螺栓的動(dòng)作,她已經(jīng)重復(fù)了整整十一個(gè)春秋。從青澀的學(xué)徒到如今工區(qū)里技術(shù)過硬的“穗姐”,扳手的重量,螺栓的觸感,早已融入她的骨血。時(shí)光倒流回十二年前,她還是那個(gè)從黔東南錦屏縣大山里走出來的苗族姑娘,帶著一身銀飾的叮當(dāng)和對未來的憧憬,嫁給了一個(gè)笑容憨厚、技術(shù)精湛的火車司機(jī)。然而,幸福的畫卷剛剛鋪展兩年,命運(yùn)的急剎車就猝不及防地降臨。丈夫在一次雨夜值乘中,為避讓突發(fā)落石,列車脫軌,永遠(yuǎn)留在了冰冷的鐵軌旁。而幾乎是同一時(shí)間,婆婆因突聞噩耗,急火攻心,中風(fēng)癱瘓?jiān)诖病煞饧蛹彪妶?bào),如同兩道從不同方向呼嘯而來的列車,在她人生的軌道上轟然相撞,瞬間并軌,將她原本平靜的生活撞得粉碎。那一年,她才二十五歲,世界在一夜之間,從五彩斑斕褪成了只有鋼軌的灰和隧道的黑。
2
醫(yī)院特護(hù)病房的紫外線燈管發(fā)出單調(diào)而持續(xù)的“嗡嗡”聲,那頻率,與她日夜相伴的隧道照明燈如出一轍,讓她恍惚間時(shí)常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在幽深的隧道里,還是在這彌漫著消毒水味的病房中。敬穗兒坐在婆婆的病床邊,手里握著的不再是熟悉的檢查錘,而是冰涼的血壓計(jì)。她握血壓計(jì)的姿勢,依舊帶著幾分職業(yè)習(xí)慣的嚴(yán)謹(jǐn),仿佛那是她賴以生存的工具。橡膠管被她熟練地纏繞在老人青紫色、布滿老年斑的手腕上,勒出的壓痕,竟與鋼軌接頭處魚尾板緊固后留下的印記驚人地相似——那是一種沉默而堅(jiān)韌的勒痕。
護(hù)士們早已習(xí)慣了這位與眾不同的陪護(hù)。她們沒見過哪個(gè)家屬會(huì)用軌距尺去仔細(xì)測量床頭柜每天微小的位移,確保它始終在“安全范圍”內(nèi);也沒見過誰會(huì)把花花綠綠的藥片,按照早中晚的劑量,一絲不茍地分裝在紅、黃、綠三色的信號(hào)燈顏色分裝盒里,標(biāo)簽上甚至標(biāo)注著類似“上行”、“下行”的服用時(shí)間;更讓她們嘖嘖稱奇的是,每天下午三點(diǎn)十五分,當(dāng)K307次列車準(zhǔn)時(shí)經(jīng)過醫(yī)院附近的鐵路線時(shí),敬穗兒會(huì)準(zhǔn)時(shí)放下手中的一切,輕柔卻堅(jiān)定地扶起婆婆,幫助她完成一個(gè)標(biāo)準(zhǔn)的45度角翻身。這個(gè)時(shí)間,是她丈夫曾經(jīng)值乘的K307次列車經(jīng)過的時(shí)刻,也是她根據(jù)多年鐵路經(jīng)驗(yàn)推算出的,防止老人長期臥床生褥瘡的最佳翻身間隔。列車的轟鳴聲,是她無聲的計(jì)時(shí)器,也是她與另一個(gè)世界連接的暗號(hào)。
3
午后的陽光透過病房的窗戶,斑駁地灑在婆婆后頸那片蔓延的老年斑上。敬穗兒拿著一個(gè)小小的放大鏡,那是她用來檢查螺栓細(xì)微裂紋的工具,此刻卻專注地觀察著老人皮膚上的紋路。在放大鏡下,那些深褐色的斑塊顯現(xiàn)出奇異的蜂窩狀結(jié)構(gòu),溝壑縱橫,如同她上周在檢修一座老舊橋梁時(shí),發(fā)現(xiàn)的減震墊上那些令人心悸的裂紋圖譜,在專業(yè)儀器下呈現(xiàn)出的老化紋理,兩者竟奇跡般地重疊在一起,都帶著歲月侵蝕和生命力流逝的痕跡。
一個(gè)念頭如同電流般竄過敬穗兒的腦海,她突然想起上周三在鷹嘴崖大橋檢修時(shí)發(fā)現(xiàn)的異常情況——幾顆關(guān)鍵部位的高強(qiáng)度螺栓根部,出現(xiàn)了一種不同尋常的暗紅色銹蝕。那些氧化鐵并非雜亂無章,而是在螺栓與螺母的縫隙間,悄然形成了完美的六邊形結(jié)晶,排列整齊,如同某種神秘的符號(hào)。就像此刻,她從醫(yī)院借來的簡易顯微鏡下,婆婆大腦CT片上那些退化、斷裂的神經(jīng)突觸,在高倍放大下呈現(xiàn)出的破碎而不規(guī)則的六邊形輪廓。一種莫名的恐懼和心疼攫住了她。她偷偷將醫(yī)生開的硝酸甘油片碾碎,極其小心地?fù)竭M(jìn)溫?zé)岬姆涿鬯铮昧烤_到每次0.3克——這個(gè)數(shù)字,相當(dāng)于她日常工作中,軌枕每平方米承重誤差的極限值,一絲一毫,不容有失。她希望這微小的劑量,能像緊固螺栓一樣,穩(wěn)住婆婆那顆脆弱不堪的心臟。
4
難得的工休假,敬穗兒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工區(qū)宿舍。第三天下午,她習(xí)慣性地打開手機(jī)里連接著病房監(jiān)控的APP,屏幕上,空蕩的病床和疊得整整齊齊的被子讓她心頭一緊。突然,畫面里的枕頭毫無征兆地開始劇烈抖動(dòng),幅度越來越大,仿佛有一只無形的手在下面攪動(dòng)。敬穗兒的心瞬間提到了嗓子眼,她抓起手機(jī),沖出宿舍,跳上了前往最近車站的通勤車。
車廂搖晃,她緊盯著屏幕,手指無意識(shí)地掐著秒表。當(dāng)枕頭的震動(dòng)頻率越來越快,達(dá)到每分鐘120次,接近她熟悉的鋼軌共振臨界點(diǎn)時(shí),她對著手機(jī)聽筒,用一種近乎本能的、帶著濃重山音的調(diào)子,輕輕唱起了那首她丈夫生前最愛哼唱的巡線號(hào)子:“太陽出來暖洋洋,巡道工兒上道忙,左看右看細(xì)打量,一顆螺帽不能放……”那旋律,是大山的回響,是鋼軌的低吟,帶著安撫人心的力量。
五十公里之外,醫(yī)院的特護(hù)病房里,心電監(jiān)護(hù)儀上的曲線正劇烈波動(dòng)。昏迷多日的婆婆,枯瘦的食指竟在光滑的床單上微微顫動(dòng),劃出的軌跡,細(xì)膩而急促,與敬穗兒日常使用的鋼軌探傷儀在探測到內(nèi)部裂紋時(shí),屏幕上跳出的波形圖,分毫不差。當(dāng)敬穗兒乘坐的列車呼嘯著穿過漫長的桐梓隧道,那震耳欲聾的轟鳴聲仿佛穿透了時(shí)空的壁壘,病房里的心電監(jiān)護(hù)儀突然發(fā)出一聲平穩(wěn)而悠長的“嘀——”聲,而幾乎就在同一剎那,遠(yuǎn)在千里之外的工區(qū)調(diào)度室里,鋼軌應(yīng)力監(jiān)測器也同步發(fā)出了一聲和諧而舒緩的蜂鳴。兩種來自不同時(shí)空、不同生命體征的聲音,在這一刻,達(dá)成了奇妙的共振。
5
康復(fù)訓(xùn)練室里,陽光透過高大的玻璃窗,灑下一地金輝。敬穗兒張開雙臂,像一只準(zhǔn)備展翅的大鳥,安全繩的網(wǎng)格在她身上投下細(xì)密的陰影。她引導(dǎo)著婆婆嘗試站立,自己則充當(dāng)著最穩(wěn)固的“安全樁”。她張開雙臂保持平衡的姿勢,讓陽光穿過安全繩的網(wǎng)格,在地面投下了一個(gè)巨大而清晰的道岔轉(zhuǎn)轍器的陰影,冰冷的鋼鐵結(jié)構(gòu),此刻竟有了一絲暖意。
婆婆穿著軟底布鞋的腳,在光滑的地磚上小心翼翼地蹭過,發(fā)出細(xì)微的“沙沙”聲。這聲響,在敬穗兒聽來,卻與隧道深處某個(gè)角落,一顆因長期震動(dòng)而逐漸松動(dòng)的螺栓,在列車經(jīng)過時(shí)發(fā)出的“噠噠”聲,產(chǎn)生了一種近乎量子糾纏般的遙遠(yuǎn)共振。它們在各自的維度里振動(dòng),卻又奇妙地相互感知。
免責(zé)聲明:本網(wǎng)站所刊載信息,不代表本站觀點(diǎn)。所轉(zhuǎn)載內(nèi)容之原創(chuàng)性、真實(shí)性、完整性、及時(shí)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證或承諾,請讀者僅作參考并自行核實(shí)。